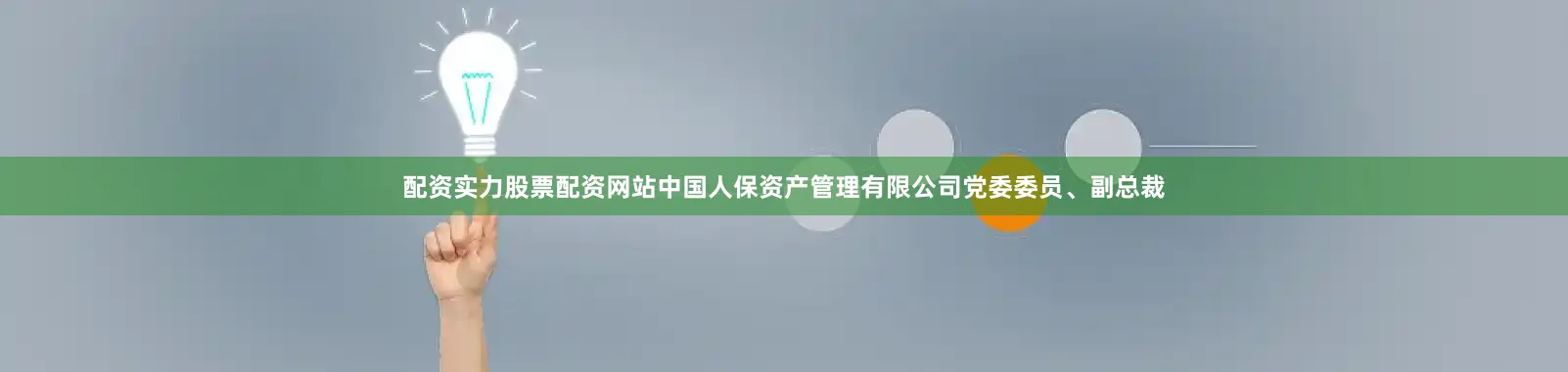对俄关系条约中的失策
清政府制定的外交策略,在涉及沙俄的问题上,仅仅取得了部分意义上的成功。沙俄陆路贸易的管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沙俄驻北京公使的职权管辖范围,总理衙门可以娴熟而又高效地与他开展外交谈判,就像与法、英、美等国外交代表所进行的谈判一样。中俄两国之间拥有着从朝鲜到新疆的漫长陆地边境线,两国政府也可以依据新设立的条约关系体系,解决对两国边界的正式划定问题。然而,第三个问题才是19世纪60年代存在于中俄关系领域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即两国对边境地区非汉族裔少数民族群体效忠取向的争夺,以及随之而来的沙俄势力介入并沿边境地区制造的阴谋策反活动。在这个问题上,总理衙门几乎是孤立无援的,因为沙俄派驻北京的公使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责任去插手边境问题,能插手边境问题的只有西伯利亚总督。
在通商口岸激起英、法、美等国商人们如此强烈妒忌的俄国陆路贸易,并没有给中国制造出太大的问题。1862年,总理衙门与沙俄驻华公使巴留捷克,在相互作出让步的基础上,签署了一份临时协定。在此后的3年内,尽管协定文本作出了某些确有必要的小范围改动,但总的说来,两国关系没有遇到太严重的困难。在上述谈判过程中,以恒祺作为主要谈判代表的总理衙门竭尽全力,经过历时14个月驾轻就熟、富有想象力的折冲樽俎,成功地挫败了沙俄准备以修约为借口将蒙古地区置于从事大规模贸易活动的全面开放状态的企图。尽管新问题层出不穷,但实践证明,双方还是能够相对容易地彼此作出调整及让步。1869年,总理衙门与俄国驻华公使倭良嘎哩达成一份最终协定并举行了签字仪式。
边界划定是一个更大的难题。1862—1864年,中俄边境地区普遍存在领土争端,双方经常抗议对方沿着整条边境线到处实施越界侵犯行为。中国官员时常会奉命前往新疆边境地区,阻止迷路的沙俄牧民及其牲畜群进入中国领土,或是前往黑龙江边境地区,将被指控越界到中方一侧割草的俄国人劝返回国。在处置此类事件时,总理衙门都尽力做到谨小慎微:对俄方哪怕是最轻微的侵犯边界行为进行抗议的同时,也会严厉处罚那些因采矿而进入边境禁区的中国人。当过错一方明显应由俄方边境管理部门承担管辖责任时,总理衙门便试图遵循以往在处理与英国之间外交问题时得到成功运用的那套政策:总理衙门请俄国公使转告俄国政府,要求俄国政府对涉事边境官员提出训诫。总理衙门发现俄国公使虽然表面上愿意合作,却声称自己无权插手边境事务。中国的边境官员会定期接到命令,要求他们必须按照总理衙门的指示行事,而沙俄外交部却从不去理解其中的暗示。曾有一次,总理衙门交给沙俄公使一封关于满洲边境问题的抗议信,收信地址是“俄国最高枢密院”。后来,当文祥拜访沙俄公使团驻地寻求答复时,沙俄公使却告诉他,公使团尚未收到西伯利亚总督的答复。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朝廷才会收到总理衙门呈递的关于沙俄主动承担边境骚乱之责,并同意派军队维持俄方一侧边境地区秩序的报告。
即便如此,中国人依旧认为中俄条约是有用的、值得去维护的。同治皇帝于1863年9月7日颁布谕令,命令中国边防官员对俄方提出的要求作出让步,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要采取任何报复性行动,因为那样做,会被俄方理解为违背条约;如果中国对沙俄实施抵抗,则中国会被打败,条约也会被彻底撕毁。所以,当前更好的策略是,自愿采取屈服姿态,至少我们手里还握有条约。
旨在勘定中俄边界的谈判还在继续。双方于1864年达成一项协议,以文本形式体现于《塔城议定书》,为解决领土争端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依据。此后,虽然争端仍继续发生,但是,每逢争端即将达到严重程度之前,双方总能通过谈判形成解决方案,据报道,双方于1869年9月10日宣告西北边界“最终”勘定。
很遗憾,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边贸协定还是勘界协议,都不能使清政府在努力将西北地区非汉族裔少数民族边民摇摆不定的效忠取向固定下来的过程中找到可供参考的明确要点,在那里,俄国人成功地成为少数民族的盟友,这几乎摧毁了中国权力的传统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清政府对这块领土的控制恰恰十分薄弱。1863年,据驻守乌里雅苏台的代理鞑靼将军麟兴的报告,在位于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之间的至关紧要的前沿防区,仅配置了24个防御要塞,总兵力由6名正规军官、30名蒙古台吉和890名士兵组成。每个岗哨的防守兵力最多不超过50人。在鞑靼将军府总部所在地乌里雅苏台,其自身的直属兵力仅有240名绿营兵和一个由33名士兵组成的满人要塞。这些人都不能被派去站岗执勤。因此,麟兴通过自己作出的一个详细的描述,强调了周边地区蒙古族人效忠取向的极端重要性。他还作出了一个推断,如果乌梁海(阿尔泰淖尔)能够保持对清政府的效忠,俄国人就无法施展其伎俩。
麟兴描述了在整个中俄边境地区普遍存在的一个基本形势——中国军队在每一处边防要点上部署兵力的名义上的配额都很少,而实际兵力数量比这还要更少。各处要塞难以控制、存在反叛倾向,原因是军费和给养连年拖欠。据中方所掌握的情况,沙俄对哈萨克人的势力影响始于1824年,彼时俄国人“诱拐”了一位哈萨克的汗王,而且直到1863年这位汗王仍处在俄国人的掌控之中;哈萨克人中使用俄语的人数日渐增多,这说明沙俄势力对我边境地区的影响范围正在逐步扩大。在关于19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方面的文献资料中,经常会出现有关沙俄军队在蒙古及新疆地区活动日益频繁的报告。
驻守乌里雅苏台的鞑靼将军明谊报告说,俄国采取了“一石三鸟”的策略:(1)“诱降”蒙古人;(2)“威慑”中国官员;(3)武力进攻。在明谊看来,沙俄的直接目标是要争取蒙古人的效忠,从而打开一条直取喀什的进攻路线。
西北地区回民叛乱的爆发,加剧了沙俄势力对于非汉族裔少数民族地区的威胁程度,沙俄的分裂宣传活动也导致了当地存在的汉回矛盾进一步恶化。随着回民叛乱范围的扩大,曾经帮助过回民的哈萨克人逃到了沙俄境内,到那里寻求庇护。面对自己领地的丧失,即使是有着长期忠诚服务于清政府记录的索伦人,也逃到了沙俄的领土上。
为遏制沙俄对边境少数民族采取的这种渗透,清政府尝试使用了各种办法,却唯独没去尝试那种有可能带来成功机会的办法。中方当然向俄国公使提出了外交抗议,但对于这些办法,总理衙门根本没有任何信心。一位困难缠身的中国边防官员写道,要想解决边境问题,只能把主要希望寄托在总理衙门,而总理衙门却回答,诸位边防官员必须自力更生,立足于自行解决问题,因为俄国公使无权指挥俄国边防官员。
对于偶发的特殊事件,清政府通常依据事态局势酌情处置。当哈萨克人逃到沙俄境内时,清政府努力采取措施,试图将他们遣返回国,从而使他们接受忠于清政府的蒙古亲王的惩罚。索伦人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们是因丢掉了生活物资、迫于生活压力而逃走的。清政府事先给他们提供了安置区域,以及用于重新购买牲畜所需的资金,还派出了一个官方使团赴俄国洽谈索伦遣返事宜。
中国人首先采取的策略,是千方百计化解沙俄势力对游牧民族的影响,继之以封官许愿争取部落首领归顺朝廷的传统办法。清政府高度重视争取蒙古亲王们的支持。当沙俄对华宣称其对哈萨克汗国的领土拥有主权时,即便是身份最低的蒙古贵族也从清政府那里很快地得到了世袭爵位。朝廷指示全体中国边防官员,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与当地部族首领协商,以便建立起切实可行的联盟。针对至关重要的乌梁海地区,朝廷给当地驻军颁布了一道关于防范沙俄渗透策反的特别公告,驻守塔尔巴哈台地区的边防官员向该地蒙古部族发布了一道内容相似的公告。
尽管如此,根据中国官员的报告,沙俄的策反宣传依旧比中国的反策反宣传开展得更为有效。同治皇帝在谕令中多次赞扬通过建立满蒙联盟来遏制沙俄的理论,指出如能争取到蒙古的合作,无异于“釜底抽薪”。但是,同治皇帝继续指出,俄国人的势力渗透似乎可以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他们正在以武力向蒙古人施压。俄国人最近又从蒙古兵营成功诱拐了13个人,这清楚地表明,满蒙防御联盟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并没有实际建立起来。
面临这种严峻形势,如果对俄采取军事报复,中国认为这并不明智,即便是在确有把握取胜的地方也不应该。中俄边境沿线地区,沙俄总体军事实力强于中方。沙俄的政治策略已被证实更为有效。清廷的政治家们精明睿智地发觉,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蒙古人的效忠应当出于自愿,否则便是无效的。清朝的领导者们没能发觉的是,他们采用的传统利诱手法——对蒙古人来说,是一种可以从外部黑暗世界逐渐走向笼罩着中华文化暮色苍茫区域的机会,身份地位也会随着自己被汉族同化程度的加深而逐步提高——再也不能与沙俄的手段相抗衡,因为沙俄提供给蒙古人的,是更有力量、拥有更高声望的生存状态,而这能使蒙古人真正成为蒙古人。
中国的决策者们在发出慨叹的同时,却也接受这个现实。自沙俄成功争取了哈萨克人和布里亚特人之后,随着回民叛乱者占领了新疆的部分城市,中国还面临着沙俄可能对其提供援助的威胁,谈判地位进一步受到削弱,至此,中国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撬动中俄边境局势的杠杆”了。因此,当前唯一具有发展前景的策略就是:(1)只要存在可能,就要与游牧民族建立良好关系,但要警惕他们有可能背信弃义;(2)改进边境管控与巡查手段;(3)尤其紧要的是,尊崇条约的法律效力,继续与俄方谈判,拒绝作出有可能使沙俄日后获得可乘之机的让步。
本文经 重庆出版社 华章同人 授权,文摘自 [美] 芮玛丽 著 吴军 译 《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
配资查询网,第一配资门户,杭州股票配资门户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